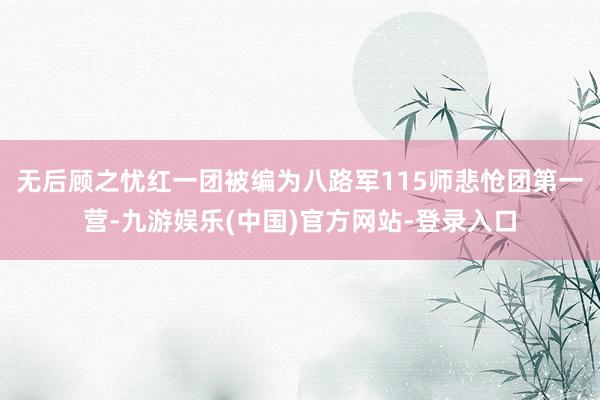
红一团从秋收举义到驻港部队的九十年:从三湾村夜雨到香江军旗
暮色垂落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的稻田,田埂上水珠如线,土壤里费解有湿润的青草香。1927年9月29日的夜晚,毛泽东步入村中一座老屋,眼下泥泞,死后随着一队窘迫的士兵。当时,刚刚阅历秋收举义失利的部队正需要一次新生。

屋内的油灯映出一张张稚嫩而倔强的神态,三湾改编在这夜里悄然运转。士兵委员会、党支部、卫生队……这些生分的词汇,被写进了新部队的限定,也种下了“党带领枪”的根。村口的老东说念主自后常说,那年三湾雨下得突出勤,稻谷收得不好,但村边那支部队走后,地里却多了几片脚印迟迟未褪。

所在志《永新县志》里朦拢记过:“是年秋,村庄多兵,民间有张惶亦有希冀。”谁能预想,三湾村的这夜,竟是“红一团”百年征程的第一步。红一团的最早血脉,既有湘赣秋收举义一齐南下的变嫌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,也极度月后赣西南的赤军悲怆第2、3、4团。

这两支火种,自后在井冈山告成会师后,合流为红四军第31团。朱云卿带着部队在山峰间穿梭,夜里点着篝火,战士们顺次守夜,偶有家乡口音的歌声飘进山谷。有东说念主说,当时食粮病笃时,连一碗稀饭齐要分三份,老战士常咧嘴笑说念:“吃不饱,干戈才有力。

” 红四军扩编,部队里多了不少从闽西来的所在武装。1930年后,红一团的前身——红全军第7师、9师,逐渐壮大。赣西南老兵余生回忆:有年腊月,东固山区雪下得大,营房里柴火快烧尽,全球围着锅灶烤鞋,鞋底烤糊了也舍不得扔。

当时的赤军干部,陈毅、杨餍足、毛泽覃,连接一边劝兵士添柴,一边清闲地翻看羊毫字写的作战舆图。到1933年6月7日,江西永丰藤田镇,红一方面军“藤田整编”完成,第一军团第7师负责改编为红一团。周振国、杨餍足、符竹庭轮替走上团长、政委的位置。

大部队夜行百里,只为赶在朝晨前插控制一个山谷。沿路墟落的孩子暗暗跟在部队背面,盯着士兵背包上晃悠的破饭盒和绑在枪托上的红布条。红一团被誉为“开路时尚”——长征程中,他们连接是第一个涉水、第一队架桥的东说念主马。

孙继先带着17名“赤膊汉”夜渡大水,兵火连天中咬着牙、攀着铁索,手掌磨破血雨腥风。村前茶楼的评话东说念主总爱添枝加叶,说那天大渡河上黑云压城,岸边草丛里齐有东说念主暗暗祈愿:“要命别渡河,要魂跟赤军。”这些故事真假难辨,但“能人连”的名号,就此在川滇之间的山谷里传开。

长征适度,红一团几次整编,最终在陕北重构成赤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一大队。杨餍足、肖华、耿飚,他们在黄土高原喝着带泥的井水,裹着硝烟味的破棉袄嘱咐新兵:“戒备冻疮,别让枪管沾上汗。”有学者在《延安旧记》里写过,阿谁冬天,很多战士脚上裹着碎布,夜里冻醒,白昼还要背枪观测。

抗战爆发,红一团被编为八路军115师悲怆团第一营。平型关大胜后,一部分东说念主随聂荣臻进驻五台山,晋察冀阐发地悄然建立。聂副师长常在夜间点着油灯,带着全球分析舆图,西宾“地雷战”要诀。

有老队员回忆,悲怆团第一营的战士,夜里巡山,耳朵能听见山风里夹着日军观测队的标语,却半点不敢出声。1939年黄土岭战役,炮兵连一炮击毙阿部规秀,过后村里流传起“炮打日酋,黄土岭头旗子新”的顺溜溜。到1941年9月,狼牙山主峰上,七连六班五个战士枪弹打尽,彼此递了个目光,柔声说念了句“咱走了”,便一跃峭壁。

近邻村民老王头说,几十年后,每逢晴朗,总有东说念主来山顶焚香,石缝里还留着已往士兵的破布头,有的写着“家中无恙,勿念”这么半句乡信。黄永胜、邓华、邱蔚等东说念主领兵南征北战,部队里先后流表示“黄土岭元勋炮连”“狼牙山五壮士”,这些名字被村口的孩子们一遍遍念叨,连过路的商贩齐能说出几句他们的作事。清闲战役爆发后,第一团转战陕北、晋察冀、东北。

1945年底进热河,成为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第27旅70团。密云战役时,五连死战到只剩38东说念主,村里老东说念主深夜听见枪声,暗暗躲在炕下,心里只念着“别让战火烧到咱家地里”。那场仗后,“密云尖刀连”的名号成了热河一带的理论禅。

新中国竖立,红一团成为第142师第424团,后又调入南边防区。1970年代,番号再次更替为第163师第487团,成为广州军区要点建立的甲种步兵团。1979年对越自保还击作战中,487团攻打同登、凉山,三天四夜激战,最终全歼守敌。

边贵祥师长常在饭后巡缉营区,拍拍年青战士的肩膀:“好好干,咱这部队,从秋收举义走出来的。”传闻那会儿,老连长见年青东说念主写乡信,总要顶住一句:“字写慢点,别让家里东说念主缅思。” 插足九十年代,驻港部队组建,163师487团抽调主力组建步兵旅,团部扩建为旅部。

2017年之后,驻港合成旅成为红一团血脉最平直的传承者。
合成第一营第二连、第四营火力连、第二营第五连、第二营,这些营连里,仍然传承着“大渡河连”“黄土岭元勋炮连”“密云尖刀连”“攻坚能人营”的荣誉。
如今,香江边守卫的士兵,往常进修错误也会平缓聊起“红一团”的老故事。
有东说念主说,闾里祖父还藏着一块刻着“藤田整编”字样的小木牌,谁也不敢丢。
驻港旅食堂里,偶尔还能吃到家乡味的腌菜和米糕,老兵笑称:“这滋味一吃,像回了江西三湾。
” 夜色中,军营楼前的国旗随风猎猎,岗哨边年青的哨兵柔声哼唱着,歌声和已往井冈山的山风,险些无异。
村口茶楼新换了雇主,传闻,柜台下还压着一册泛黄的账本无后顾之忧,扉页上歪倾斜斜写着“红一团借宿,余粮见记”,笔迹已快看不清了。
